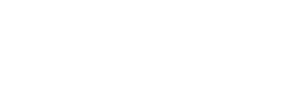两岸、三地“社区支持农业”的三种呈现
发布时间:2014/12/17 现代农业 浏览次数:708
这年头,好像只有雾霾和毒食可以带动全民一起关心可持续发展。可是,老百姓对雾霾能做的事情还太少,连它的源头都莫衷一是,但对食品安全问题,数以万计的人已经行动起来,让一场可以从一家一户、一田一畴开始去改变大环境的运动悄悄发生。这种静默的力量来自于食品问题的日常性,这种源自日常生活的力量使得中国大陆的“社区支持农业”运动迅速发展,并且能够与起步更早的台湾和香港的CSA实践等量齐观,有能力对话。
“社区支持农业”这种另类食品流通模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同时兴起于欧美和日本。当时,疯狂的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和所谓“绿色革命”制造的“化学农业”和工业化农业一方面造成了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另一方面让农民失去对农业的控制,生计艰难。面对这些,一些城里人行动起来,他们直接去找农民,向他们订购遵循生态原则生产的农产品。这些订单往往是长期合约,预先付款,价格较普通市场价优厚,并且与农民共担生产风险。这样,农民和消费者组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相互关顾,因此农民有了足够的条件去用生态方式生产健康的食物。这种模式,在日本被生动地称为“提携”,在一些欧洲国家,也被叫做“团结农业”。
CSA在两岸三地的实践已经持续了二十年。今年四月,香港社区发展机构“社区伙伴”出版的《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之甦动》一书,难得而有趣地将两岸三地的CSA历程并置起来,让人仿佛在观看一本植物学图谱—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环境中生长,长出来的虽然还是同一种植物,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特征。
台湾的社区支持农业受到日本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生活者运动”的影响,成规模的实践始于1993年台湾主妇联盟的成立,当时主要关心的问题也是在因为闷头追求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而污染了环境的台湾该如何保证食品的健康。而在2002年台湾加入WTO之后,本地农产品在涌入的进口农产品面前彻底失去竞争力,农业被政府视作失去意义、等待切除的阑尾,乡村面临快速的非农化,而此时人们意识到台湾的农业过度依赖进口,维持本地农业对于确保基本的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也有一些人,比如赖青松,提出农业的不可被化约为经济价值去看待的人文价值,它包含着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回答着“我们是谁”的问题,它在这个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平、年轻人越来越深地被资本压榨的年代,提供着另类生活的出路,回答着“还能怎样生活”的问题。
香港的社区支持农业在上世纪90年代有过一些零敲碎打的实验,成熟则是在2000年至2003年之间。虽说港人也经历过毒菜事件,但这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焦虑,以至于成为推动CSA发展的主要动力。香港的CSA,长期与一些香港人在激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对邻里关系、社区纽带和本土生活方式的珍视与守护联系在一起。CSA试图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团结合作,创造本地经济。而在香港这座只有极少农地的“石屎森林”和什么都依赖进口、零售业过于发达的“自由港”实践CSA,意味着直面其九牛一毛并且还在萎缩的农业、农地和乡村社区,逆潮流而动,去实践曾是生活常态如今却踪迹难寻的“本土经济”,重建被城市化和现代商业割断的社区纽带。因此,CSA在香港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尤其当“地产霸权”一步步侵蚀农地、淘汰农业、瓦解乡村社区的时候,CSA开始有意识地与社区保育运动相互结合,展开立足日常生活的抗争,从中创造关于“本土价值”的话语,来追问香港的文化身份和发展伦理,同时探讨作为个人,何以能够摆脱资本为他(她)设计的人生棋局,过上自主的生活。
大陆的社区支持农业大约在2003年开始思想播种,2006年前后才真正破土生长,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一股强大的“服务三农”的思想源流,至今也仍为一些在这个领域内开展工作的学术机构和NGO所高举。而近几年来,尤其经过2008年三聚氰胺奶事件和2011年一系列非法食品添加事件的刺激,公众对食品健康乃至安全问题的严重关切,让CSA实践中的“食物关切”远比“三农关切”更加强烈,成为社区支持农业在大陆发展的最强动力,同时也使对三农问题的关切终于开始赢得越来越多的意识觉醒的城市消费者的支持。因此,一批能够积极地迎合与调动城市消费者的农夫市集和CSA农场,成为大陆CSA最强有力的推动者。而在迎合消费者心态和需求的同时,开展逐步深入的消费者教育,不断指出食物和环保、三农等社会议题之间一体多面的关系,让CSA保持改变社会的理想而不被消费文化消解,是这些实践者正在面对的课题。
同一种思想种子,被三地的人们种到了各自的社会土壤里,用它来面对自己社会的议题。但这些议题并不专属于谁,而是存在于其中每一个社会,只不过轻重缓急不同,因为三地的社会都同样面临着全球化和发展主义给农业带来的挑战,而农业所关乎的,又绝不仅仅是“吃”。
文章来自金银岛农业
下一篇: 干货:如何加快构建现代农业新型经营体系?